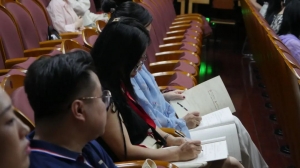2024年7月23日在流金铄石大暑到来之日,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二胡表演艺术人才》专题系列讲座也进行到了如火如荼的第二周!在此,我们全体学员由衷地感谢本次项目的负责人汝艺教授和主办方上海音乐学院的大力支持。汝老师被大家亲切的称为“牵线塔桥”的伯乐与指引每位青年才俊人生方向的领航者,能够遇到这样一位良苦用心、大爱无私的好老师实属不易和内心不断涌动着的感恩与感动。
满满一天、精彩纷呈、高屋建瓴的理论讲座由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红色音乐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音乐艺术》副主编、《人民音乐》特约编辑、《音乐研究》编委、原解放军艺术学院科研部部长兼音乐系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主编、著名的音乐评论家、博士生导师李诗原教授倾囊相授。李诗原教授在音乐界是非常著名的专家,在全国的各个高校是争相邀请的人才。也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的主编,主持重大的社科、国家各方面的重大项目,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科建设、理论建设等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李教授尤其在红色革命历史体裁无论是歌曲、歌剧、原创、传播等方面有着深厚的研究。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李老师来给我们做专题讲座。讲座全面围绕《民族器乐的创新发展——发展现状、历史经验、理论启示、发展对策》和《民族器乐的存在方式——中国传统器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依据、文化传统与现实需要》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解读。对于当今多元化、信息化、现代化时代下的我们这一代人如何把这个交接棒更好地接力下去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李诗原教授今天的课题是在2021年承担的中宣部项目中所研究的方向——民族器乐,该项目团队研究了近两年时间。作为项目的主持对民乐方面有深入独到的研究,今天李老师把这些研究成果带到课堂引经据典、纵横捭阖、谈古论今、洋洋洒洒与学员们共享。
壹
民族器乐的存在方式——中国传统器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依据、文化传统与现实需要
首先,李老师从民族器乐讲起提及两个词语“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两个词语的出现是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新辉煌。主要是针对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时的提法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后来简称为“双创”。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就要理解什么叫做“双创”。“双创”和我们过去的继承、发扬有一定的联系,更为明确。可以认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继续发展存在的一个重要方式。对于现代文化发展的方向,关于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问题,李老师对党中央精神理解的非常深刻。他讲到:这十个字里每一个字几乎都是在变化,我们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不是“复古”,也不是“反古”,更不是要“重古”。“双创”就是创新,就是变化。就像我们今天的二胡艺术一样永远在发展,永远在路上。“双创”如今已经不只是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域,对所有的文化我们都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创新的态度。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在新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都应该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艺、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二点李老师谈到民族器乐概念的鉴定。作为一个理论范畴是中国乐器演奏音乐的总称。它所对应的是西方的器乐,这里面有独奏、重奏、合奏等。中国乐器的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期它的呈现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很多乐器都不是本土的,而是从西域流传过来逐渐成为中国乐器。中国乐器也不一定都是要在中国土生土长。无论是从哪里生产只要最后在中国形成其作品、演奏家、理论体系就是中国乐器。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认为在文化程度来讲,我们的国界早就突破了,是无国界的。但是我们的民族性是永远不能丢的。中国的乐器里面也包括56个民族的民族乐器,不光是汉族。其中包括三大类型:第一大类古代器乐及其当代遗存,这个遗存在今天得到很好的发展,是我们中国音乐家引以为荣的具有九千多年历史,从河南舞阳贾湖骨笛的文物出土考古发现得以见证。二胡这件乐器真正的作为独奏乐器的时间也就是一百多年,从刘天华的第一首二胡曲开始。是比较年轻的乐器,与乐器本身的发展是有关系的。拉弦乐器具有技巧化特点,发展的较晚,与西方国家有相似性。第二大类民族民间器乐,是我们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仍然活在民间的合奏音乐,也称之为乐种。第三大类现代民族器乐,以刘天华为代表的民族音乐演奏家所推进、所创造出来的,借鉴西方作曲技术深沉的民族器乐。前两类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中国传统器乐,而现代民族器乐属于新音乐的范畴。刘天华的二胡曲中明显借鉴了小提琴的演奏方式,从曲式结构、音乐材料的运用上都得已体现,最为典型的就是《光明行》。每一个时代都有大师级的人物推进民族器乐的“双创”。
任何一种音乐样式它的存在方式都是不断变化、运动的。世界万物都是在变化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讲到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时有规律的,静止的东西是不复存在的。我们的民族器乐始终是在变化中存在的,不变是相对的,变是永恒的。在漫长的、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于传统器乐也好,对于现代民族器乐也好,“双创”都是它的存在方式。也可以讲没有中国传统乐器就没有今天的民族器乐,没有对传统器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没有民族器乐。李老师还为我们梳理民族器乐各乐种的历史脉络、发展历程及乐器改革。介绍即将出版的四十万字书籍科研成果的主要内容。分别从导论民族器乐的存在方式;上篇民族器乐的文化传统,即民族器乐的物质基础、民族器乐的形态特征、民族器乐的文化精神;中篇民族器乐的发展历史,即中国古代器乐的历史与形态、中国近现代传统器乐的发展、中国传统器乐在当代的发展;下篇民族器乐的当代呈现,即中国当代民族器乐独奏、中国当代民族器乐重奏作品、中国当代大型民族器乐作品;以及结论民族器乐的创新发展。李老师谈及中国乐器演奏光看谱子是拉不出感觉的,还要讲究音色、手法等。民族器乐总体上代表着中化传统文化精神,中国文化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自古以来“一点四方”的概念它的形成与中国的政治有关系。地域文化是我们民族器乐产生的重要源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对民族器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里面与自然条件、宗教信仰、民间风俗是有关系的。作为民族文化的民族器乐,是中国五十六各民族的民族器乐。这种中原和少数民族混融的、并存的、固生的特点,在古代就已经体现出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我们党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民族大团结的概念。所以民族文化的概念在民族器乐中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民族器乐也是多民族器乐,是不同民族文化的一个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乐器是不断地多元,分类更为条理。中国器乐也像其他的艺术一样经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民族器乐、民间乐种在原有的基础上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中国传统器乐从远古先秦、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在到近代五个时期的发展,构成了我们民族器乐的历史。一种风格、一种流派的形成应该有作曲家、演奏家、新作品地不断出现,最重要的是形成它的创作、表演、传播、理论体系化的发展。李老师强调作为任何一个乐器没有炫技是不行的,但是过于的炫技也是不行的,尤其是当炫技和表现是脱节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技巧都应该与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之间形成一种匹配,炫技是不能脱离艺术表现的。民族器乐中多部作品试图用民族乐器的音响及表现中国书画中笔画的高挑、着色的墨趣等神韵。
还谈及本世纪党的十八大以后新时代大型民族器乐作品及创作特色,在讲到民族管弦乐队每一个组别高中低三个层次的构建,乐队演奏出来的音响是非常丰厚的、有底蕴的。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民族管弦乐队里面的律制统一和音高的问题仍然是今后想办法探索去解决的问题。除主旋律和对技术的超越之外,还有一个多元跨界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视觉艺术、舞台艺术、舞台演剧的表现手法逐渐的到民乐作品中来。李老师认为这样一种多元的、全方位的舞台演剧式的表达并不一定能使中国民乐得到健康的发展。中国民乐的健康发展应该回到《长城随想》这样一种位置上,真真正正的用器乐的表现手法来取胜,而不是图个视觉或者文字,找一些花里胡哨、哗众取宠音乐之外的因素。
世界任何事情都是久分必和、久和必分,音乐也是这样。音乐以及多维艺术都是从分离走向综合,综合又走向分离的过程。中国传统器乐的基础是中国民族器乐的文化底蕴。我们无论如何去创造、去发展、去转换、去创新都不能脱离这个基础。这个基础是物质基础,脱离这个物质基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讲其他的一切都是妄谈。这个物质基础就是我们的民族乐器、民族乐队、民族器乐的乐种。李老师提出乐器和乐队包括乐谱我们应该怎么去保护它、整理它,这里面有很大的学问。我们应该有多大的能力去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去保护传统。我们在对一个经典的作品、对一个传统的东西进行现代呈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保护、保存它的原貌,而不是所有的都是“新瓶装旧酒”的方式。我们的乐器改革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我们的民乐如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如何搭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当前在舞台上到底怎么去呈现我们的民族器乐。怎样才能使一种文化既保持创新发展,又在变化不变当中保持其本质特征和原有的文化特征。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条件下究竟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思索。
乐器改革、乐队组合、乐谱的整理和保留我们都应该保持一定的速度、一定的分寸,而不是没有底线、无限制的改动、扩展。如果创造、创新、发展、转化没有限度的话,我们的传统也就不复存在了,那么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也将成为一句空话。我们要保留民族器乐的文化精神,尤其是民族器乐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这一点不能切断。没有这个文化根基,表面文章做的再好,也不能表现中华文化的精神。民族器乐的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通过历史发展看到中国的传统器乐都是在不断的吸收外来文化,把外来的东西变为自己的东西。我们应该善于从历史中间找到成功的经验,包括乐器改革的经验、鉴别乐队的经验、重要是音乐创作的经验。
从历史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延续到今天,它的内在动力就是“双创”。它是保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展,同时不究其本质的文化机制。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中华文化变的特质和基因自古以来就有的。任何文化存在都是变化和运动中的存在,归根结底也是人的存在。人永远是在变的、社会在变、人所生存所依赖的物质条件、精神世界都在变,人是在不断地改善和优化自己的生存状态,在这样一种过程中文化作为为人服务的东西也在不断的变化。这就是“双创”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文化要维持自身的发展,不发展就会僵化,只能成为文物。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使一种文化保持不变,要立足求变。传统应该为当下服务,文化传播、传承中间的差异性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的民族音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物竞天择的结果。作为民族音乐工作者只有与时俱进、同时保持传统的根基,顺应时代发展,我们自然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大众的尊重和喜欢。李老师提出我们在创造性转化方面还有待提高,万变不离其中,即“移步不换形”。很多人都是从审美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去思考音乐的功能、价值,但是很少去思考音乐的本质。它对于人而言意义究竟何在,除了审美的愉悦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吗。音乐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应该是保持一种集体的民族精神,应该保持总体的人文价值取向。总而言之,传统器乐的“双创”是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做学问也好不能只是埋头拉车,应该抬头看路,要回应党和国家对文化问题的重大关切。我们今天举办闵惠芬二胡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的目的也是如此。
贰
民族器乐的创新发展
——发展现状、历史经验、理论启示、发展对策
民族器乐创新发展,如何去发展,我们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历史经验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理论启示是什么,发展对策是什么,课题研究最终要达到的一种目标就是研究的课题应该要给国家、相关部门提出一个思路、一个决策执行。李老师对发展现状还是有一些忧虑的。民族器乐是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器乐艺术,同时又是一种不断接收外来文化滋养而创新发展的音乐文化。至二十世纪已经形成多元并存的状态。李老师认为中国传统器乐在时代浪潮的当局之下,是陷入困境的,只能在夹缝里生存。尽管我们最近十几年来对弘扬传统文化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是我们的任务恢复,在全国各地的情况仍然堪忧。我们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条件都在改变。所以时代在变,我们的传统器乐、传统丢失这个是一个自然现象,我们要认识到。另外中国现代民族器乐是比较顺应历史潮流,它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中保持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二胡、现代民乐较为繁荣。尤其是这几年民族音乐的发展在一种政策性引导之下创造很多新的辉煌,不断涌现的优秀的民族器乐作品从一定程度上推进二胡音乐在二十世纪文人化的一种发展。二胡音乐从民间的、传统的这么一个戏曲的伴奏乐器或者是民间乐种里面的合奏乐器,由刘天华本人逐渐的把它发展成为独立的乐器,并为此创作了专门的独奏作品。是二胡音乐从民间到专业的跃升。在建国以后我们民族器乐发展趋势从民族化、民间化、文人化、革命化到二十世纪初的流行化转变。从技术的角度、表演的角度来看,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闵惠芬大师探索和提出的“器乐演奏声腔化”的发展。
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倾向于一种自然规律,人是造不了文化的,但是文化可以造人。我们要慢慢去变换、改变、顺应、接受。民族器乐并不是一个封闭性的概念,不是僵死的,而是开放的、不断被构建的、21世纪有它独特的理解。实际怎么去发展不是理论家规定的,也不是民乐家去规定的,而是社会综合推动的结果。理论有的时候不一定指导实践。音乐对人的人文关怀最重要最根本的应该体现音乐界如何缔造一个特定时代人所需要的人文精神这才是根本。我们需要在音乐传播方面多下功夫。这里面有很多演奏方面的跨界现象、包括炫技等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要搞好民乐,我们的音乐教育、人才培养是关键。民乐的传播现在已经进入到自媒体时代、全媒体时代,因为娱乐的方式在增多,群众性的民族器乐活动有弱化趋势。我们作为职业音乐家和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去正确引导,追求应该追求的目标。最后李老师强调要加强音乐评论及其健康发展的问题。批评家要敢于说“不”。
没有好的作品,没有好的演奏家,一切都是一句空话。综上所述,民族器乐的发展在新时代的继承上离不开理论家、教育家、评论家、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以及乐器制作家和大众欣赏共同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讲求“天人合一”,即天道。天即自然界,道即为规律,天道与民族器乐的发展相合,必将与天地共存,日月同辉,坤尽复来,在创新的道路上继续大步向前不断地发展和代代更替中传承下去。